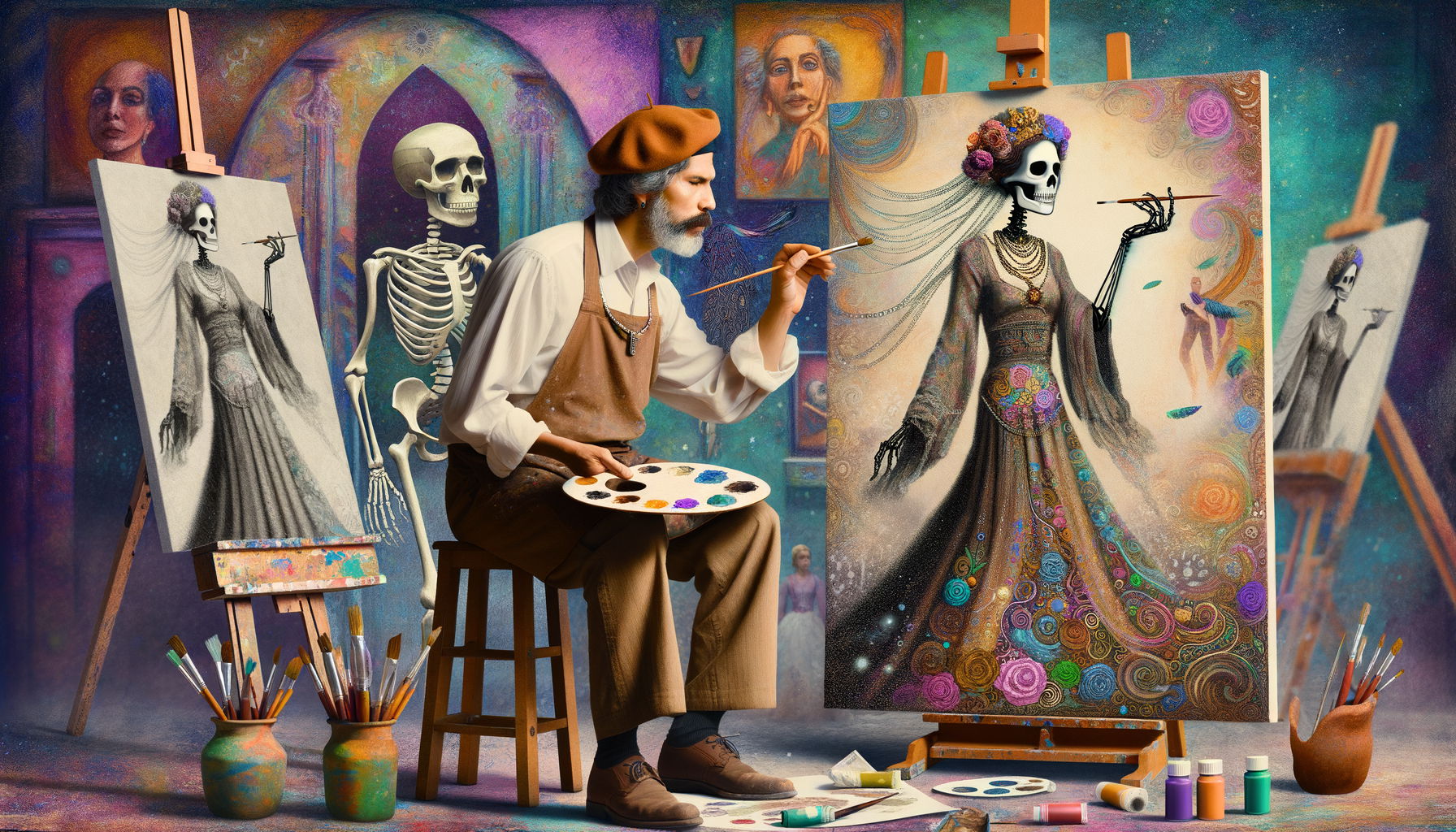

学生们拿着 985 的分,去考“双非”校,听着就悲哀。
学生们拿着 985 的分,去考“双非”校,并非家长逼迫,而是学生自愿,听着更悲哀。
学生们拿着 985 的分,去考“双非”校,媒体感叹青年人理想主义破灭,矛头直指张雪峰们,听着哀上加哀。
现在流行 “讲故事” 。学生们拿着 985 的分,去考“双非”校,被说成张雪峰们“讲故事”的结果。
然而,一种社会现实如果不在,故事何以讲得出来?
据说一种建构论是这样的: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建构的,可以这样建构,也可以那样建构,总之,现实怎样无所谓,只要把故事讲好就可以了。
某河南小伙,19 岁,第一次出门打工,到上海。虹桥下火车,打车去浦东,车费 100,扫码支付时手抖,付了 1010。后来,向司机索要多付的钱,司机不理,拉黑。再后来,到派出所报案,警方只告知了他车牌号,没有司机号码,也没帮他联系。最后,他吞药自杀。
这个故事,该怎么讲才好?
看起来,指责死者玻璃心、抑郁症,将这一事件淡化为罕见个案,应该是对某些目标伤害最小的策略。这样大家便可以继续假装活得很好很安全。
更重要的是:
该不该以“给现实整容”为己任?
这个问题对咨询师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尤其对人本主义之后的咨询取向,积极心理学,后现代取向的咨询,一不小心就将积极关注变成了美化现实,甚至否认、取消现实。
这将使一个咨询师变成一个江湖骗子。
存在即是被感知。望文生义的话,很容易将这句话误解为感知之外,并没有所谓外部世界。做如此解读的,应该都没认真读过贝克莱。
我发现自己仍是一个朴素的实在论者,我相信外部世界存在,并且这不需要辩护。 外部世界存在,是一切的起点,同样也是一个人可以质疑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起点。你无法谈论一个本来为“无”的东西。当你意识到自己不知道某些东西,你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关于这些东西的某些东西,否则你就不会有不知道的意识。
故事的起点一定是:外部世界存在。 认知疗法期望通过改变人的认知而改变自我;叙事疗法期望来访者自己改变对其人生故事的讲述而改变自我。然而,这都不意味着在贝克或者怀特看来,一切都只是人的意识、认知、观念、文化传统,除此之外,一切皆无。
如果一个人的认知竟可以不依赖于存在而单独起效,那么便有理由通过某种办法将某个“完美故事”灌注到他的心灵。这便是历来的江湖骗子、邪教、洗脑者的传统孜孜以求的境界。
改变认知,改变自我叙事,的确可以改变自我。然而一个人的认知总是和他的存在交融在一起的,甚至根本上他的认知与他的存在本来就并非两个,而是一个。
来访者的认知也好,叙事也罢,都来源于他自己的真实经验。 你无法取代他的经验,只能在他的经验基础上,以咨询师的方式影响他,使得他重新整合这些经验,这便是疗愈,经验还是那些经验,只是重新整合。 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与后现代叙事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咨询师与江湖骗子的区别,根本上就在于“故事”是谁的、是由谁讲述的。 故事是来访者的,讲述、重述故事都是来访者来做的,这便是咨询师的工作方式;故事是“大师”的,讲述、重述故事都是“大师”来做的,而且不许你接受别人的故事,这便是江湖骗子的工作方式。
近年来,脑后插管、基因改造的拥趸似乎越来越多,江湖骗子们似乎又从中看到了希望。
这里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能否实现,实话说,当你并不把一个人当作人,可以对之为所欲为,技术上便可说没有什么门槛。
科学的界限,是且本该就是由人文划定的。 否则,你所创造出的便不是新人,而是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