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称“引论”,《精神分析引论》却是弗洛伊德 1916 年的作品了。此前,自《梦的解析》开始,作者的研究覆盖日常失误行为、梦境、笑话、文学、图腾禁忌等,精神分析的体系基本成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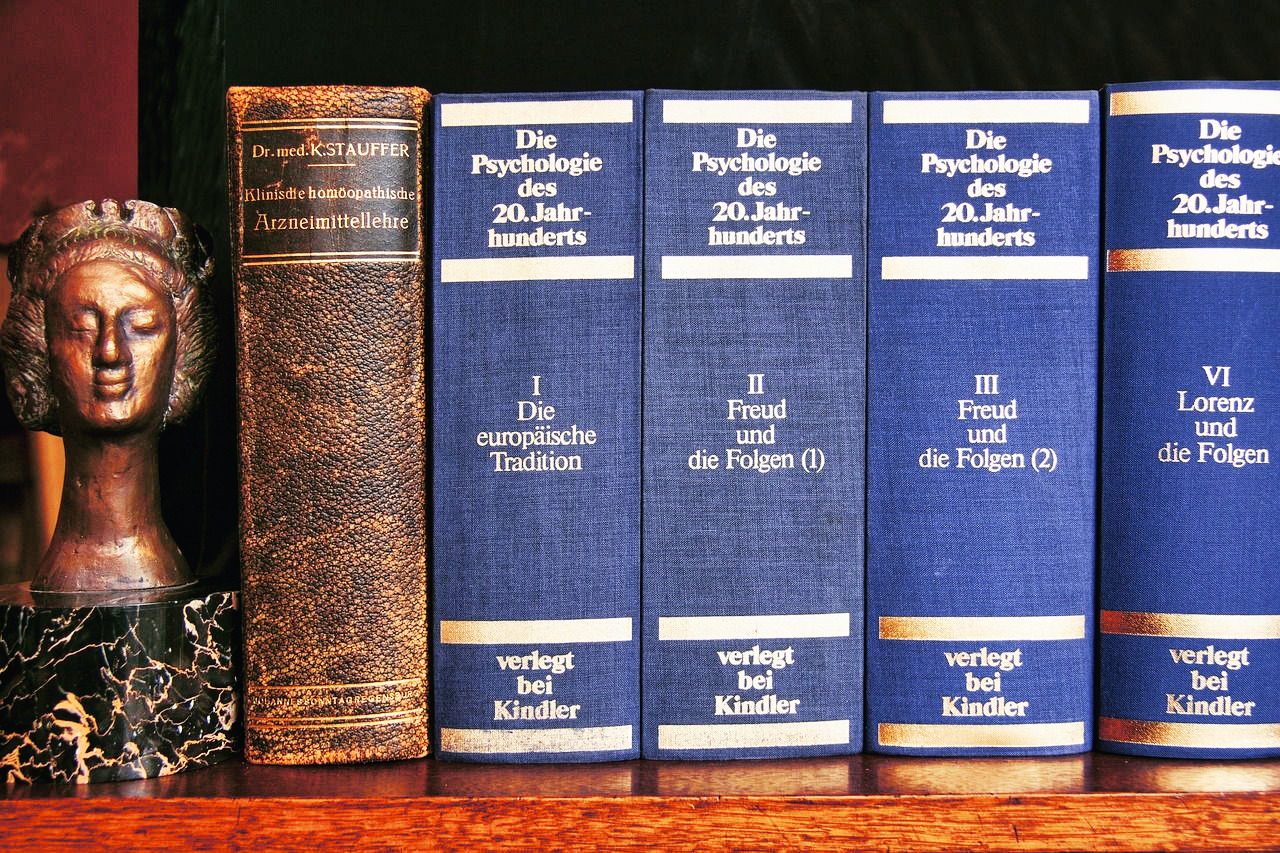
在我看来,19 世纪的经典作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从基本经验出发形成某个基本假设,层次递进,最终描绘一个被认为是可以进行预测的理念体系。马克思就是从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制造出各种概念,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弗洛伊德也是如此。他从潜意识这个基本假设出发,过渡到日常生活的失误行为、梦、神经症,明显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路数。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声称自己是在做着某种“科学”,或者,有理由相信他们都自认为自己的学说就是科学。马克思几乎穷其一生都在大英帝国的图书馆里写作,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几乎为 0,但是他声称自己的学说是科学的,而欧文这类实践者,反而被认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弗洛伊德自己其实对精神分析是否具有科学性怀有某种焦虑,因此在书中,他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学说辩护。然而,其中有些辩护,仅仅因为弗氏的能言善辩,而显得有些道理,深究之下,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为了辩称自己学说的不确定性有理,提出的理由是某些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是模糊的。事实确然如此,但这个逻辑只能证明精神分析与科学都具有不确定性,却不能证明精神分析满足于一些不确定的推断就是合理的,同时另一方面,科学在努力消除不确定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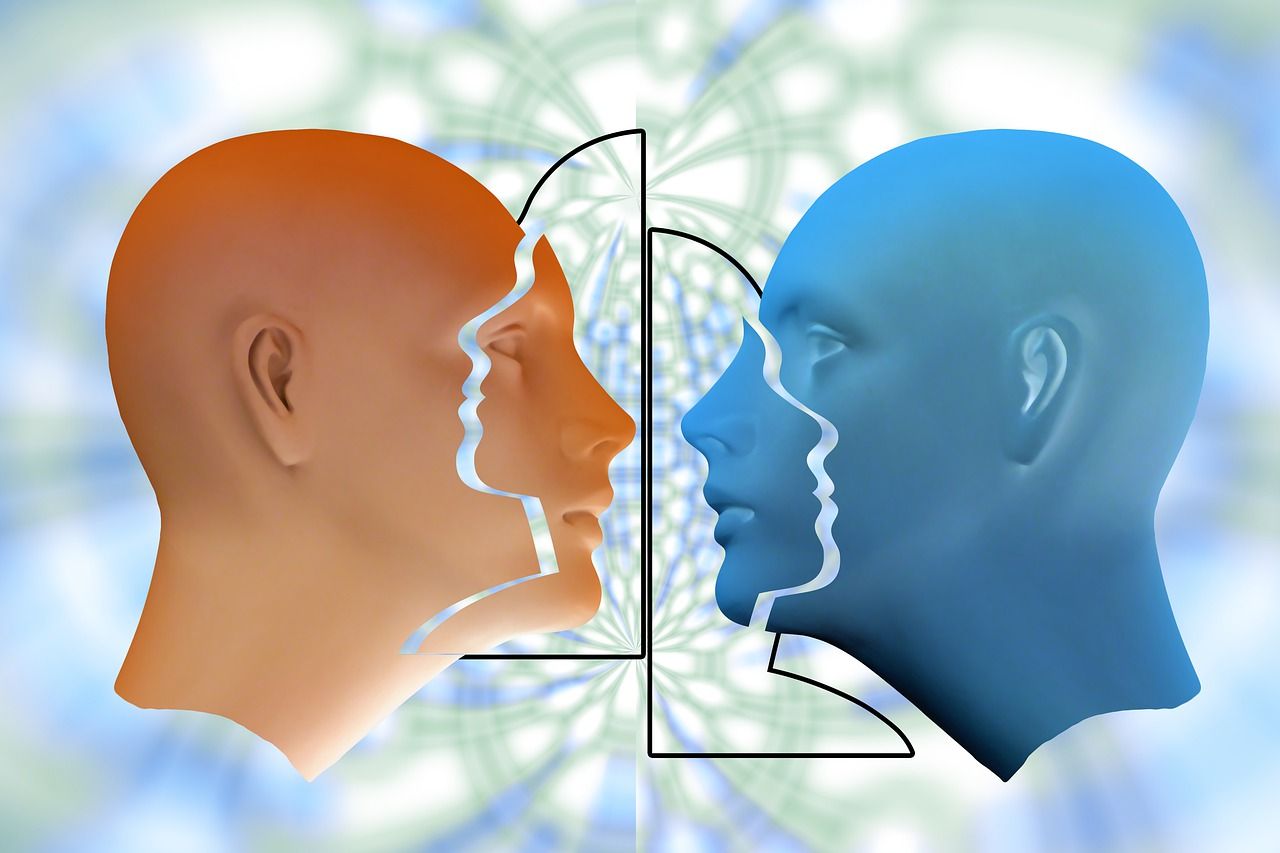
实际上,精神分析的科学性一直是个问题。很多反对者提出的理由都是基于精神分析不科学这个判断。最主要的批评是它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有趣的是,如果一个科学主义者持这种立场来批判精神分析,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某些声称自己持有反科学主义的后现代立场的批评者也拿这个理由来批评精神分析,其立场颇为令人费解。而目前很多精神分析的辩护者,也在努力证明精神分析可以是或者就是科学的,依恋理论和心智化治疗,被看做具有循证品质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回击,似乎也并不很有力量,无法阻止精神分析在西方的日渐式微。
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价值与精神分析是否科学绑定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如果我们把科学认做以揭示真伪为目的研究,那么精神分析并不是这种研究——尽管弗洛伊德的确相信,或者至少想让他的学说成为科学。说到底,一件事物的价值,并不必然取决于它的真假。认为真实才有价值,虚假没有价值,这只是我们没有根据的预设而已。


如果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就会看到潜意识本身作为精神分析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本来就不必具有必然的真实性。精神分析师给予来访者的诠释,也不必具有必然的真实性。诠释的目的并不是“说中”来访者潜意识里真有的某些东西,因为“潜意识里真有的某些东西”每一个字都是假设。这正如《红楼梦》,它打动我们,是因其文学性,是宝玉黛玉等人的命运悲剧,而并不是因为它是曹雪芹的家世小说,并不因为它可以还原为曹雪芹自己的真实事件。毋宁说,诠释是一种主体间寻找视域融合的努力,它可以完全是虚假的——如果真有那种确定的真实的话。可以简单理解为:诠释(以及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分析等等)所追求的,就是那个“啊哈”的一刻。这比诠释内容是否真实要重要得多——还是要说,如果真有那种真实的话。其实催眠在寻找的,也是“Aha!”时刻,弗洛伊德认为催眠阻止了来访者探寻潜意识里的真实,所以放弃了催眠,这无疑说明他真的相信潜意识作为实体的存在性。但其实如果“悬搁”起这种真实,催眠,以及几乎所有的咨询技术,都可以在一个现象的层面找到共同的目标,哪一种,都不必然要被放弃。
总之,与其纠结于精神分析是否具有科学性,还不如承认精神分析是一种结构化、体系化的叙事。它并不具有确定的科学性,也不像叙事治疗主要依托于来访者自身的个别建构,它既是叙事的,也是结构化的,它可能不具真实性,但它也不是某种随意的创作,它有他自己的体系,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自洽的要求。当然,也因为这第一点,精神分析难免(即使是不自觉地)要求来访者削足适履,去符合它的某种体系,而这又是后现代叙事、合作对话等等认为一直应该保持警惕的。


根据哥德尔定理,一个命题体系,要么不全真,要么不完备,二者不可得兼。精神分析也概莫能外。在我看来,精神分析只有放下自己是否科学的纠结,才可能找回精神分析的“自我”,回归精神分析的“天命”。这并不会影响到精神分析的价值,反而可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弗洛伊德限于他的“历史局限”,或许不能接受这个方向,后世的继承者却可以不必抱残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