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全人类,“抑郁症”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7 年估算,全球共有约 3.5 亿抑郁症患者;2019 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发表在《柳叶刀》的研究文章显示,在我国,抑郁症终身患病率为 6.9%,总数量估算超过 9500 万,与 90 年代初相比,增长了 100 多倍。
另有研究显示,抑郁症已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健康第二大杀手,以增速看,大约 2030 年它就将“修成正果”,成为“杀手之王”。
然而,对于国人,特别是 60-70 年代的中年人,抑郁症就像突然跳将出来的一样,此前似乎从未听过这样将“想不开、不高兴”也叫做“病”的咄咄怪事。
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抑郁症是一种实在意义上的疾病,但也有一些人觉得身边的抑郁症患者其实也并非想象中那么多。
这些疑惑之中,其实潜藏着很多值得掰扯掰扯的东西。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线、或是一个圈,总之是分割正常人与病人的一个工具。
然而,由于缺少明确生理诊断指标、症状学诊断标准日益宽松、相似症状掩盖病因的复杂性,诊断标准对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影响了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与目前排名第一的大杀器“癌症”相比,抑郁症的诊断有很大不同。
因为癌症一般有个“看得见”的标准,比如 CT、B 超、MRI(核磁共振)等等,就算最普通的 X 光,虽然往往看不清楚,但好歹也能算是“眼见为实”了。
抑郁症则不然,虽然现在的研究已经到了神经回路的水平,貌似也找到了杏仁核、海马体、扣带回、五羟色胺、多巴胺等 N 个“嫌犯”(这些都是什么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是,由于作用回路多、个体影像形态差异大,将单个生理指标的异常作为抑郁症的诊断标志,却还差得远。这可能也是某些人不太愿意相信抑郁症也算是病的原因之一。


没有靠谱的生理指标,于是只能采取“症状学”的诊断标准。
所谓症状学标准,其实就是建立一个症状集合,这个集合是大是小,当然就意味着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是多是少。
然而很不幸,这个症状集合里的元素似乎经常变动。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是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也就是著名的 APA(发过心理学论文的一定知道这个)出版的诊断标准,目前最权威、最流行,然而 DSM 也常常改来改去。
比如,DSM-IV 比之 DSM-III,做出抑郁症诊断要求的病程大大缩短,DSM-V 中取消了 DSM-IV 中将居丧反应(也就是亲人丧失之后产生的情绪低落)作为抑郁障碍排除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月经前期抑郁障碍”。
可以明显看出,能进入抑郁症圈子的门槛越来越低。
原来需要病上几个月,现在只需要 2 周;产后抑郁、经前抑郁、甚至只需要“恶劣心境”,就可以获得抑郁障碍的标签。
可以想见,DSM-III 作为标准时,抑郁症显然没那么多,DSM-IV 时就多了不少,DSM-V 就更多了,DSM-VI 如果再放开……
但这是好事吗?想象一下,在 2013 年 5 月的一天,你的亲人去世了,你为此感到悲伤,你去问医生,医生告诉你这不是病,按 DSM-IV,这不是抑郁症,于是你回家继续悲伤,然后过了几天,医生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你可能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们现在采用 DSM-V 做诊断了——你是不是抑郁症竟然是由标准说了算,而不是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病?这真的合理吗?
另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想找到抑郁症的生理病因会因为诊断标准的“兼收并蓄”而更加困难——你都不知道你治疗的还是不是同一种病。
张三咳嗽是气管炎,李四咳嗽是肺结核,王五其实恶性肿瘤,赵六其实主要是觉得偶尔咳一下比较有风度。然后你把他们都当咳嗽治,就可以吗?
同理,百忧解刚刚上市,治的可能是抑郁症(虽然当时的诊断标准也很模糊),但这药用到今天,治的还是当初那种抑郁症吗?它还管用吗?
所以,症状学诊断本来就不那么精确,如果症状再成为大杂烩,那就更少科学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不管症状背后的病因如何,具有相同的症状就可以当作一种病来治,对于这种观点,读者或可自行思考它合不合理。
医生
医生是做出抑郁症诊断的人。相信我,这绝不是一句废话。
医生手头可用的工具,对诊断标准的掌握情况、可能避免负误诊责任的动机、医生手头是否有可用药物来应对病症、资源稀缺情况下提升诊疗效率的需要,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你是否会被判定为抑郁症患者。
从伦琴、居里夫人等人的伟大发现开始,影像学诊断几乎改变了医学诊断的面貌。
精神科医生手头的工具却还是相对比较“复古风”的,DSM 是权威工具,但权威工具不见得就是好工具。 这好比人家拿着机关枪,你拿着红缨枪,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MRI 被发明出来以前,有经验的神经内科医生,可以通过让患者做出指定的手势来判断患者是否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病等神经疾病,但是对抑郁症,目前一般还是“主要靠问”,辅以量表验证。
问诊和填写量表都很难完全避免主观。 这就与医生个人相关了。尽管都是参照 DSM 的标准来问,但是医生的问法、对病患信息的接收与诠释、甚至自身情绪等等都将影响他的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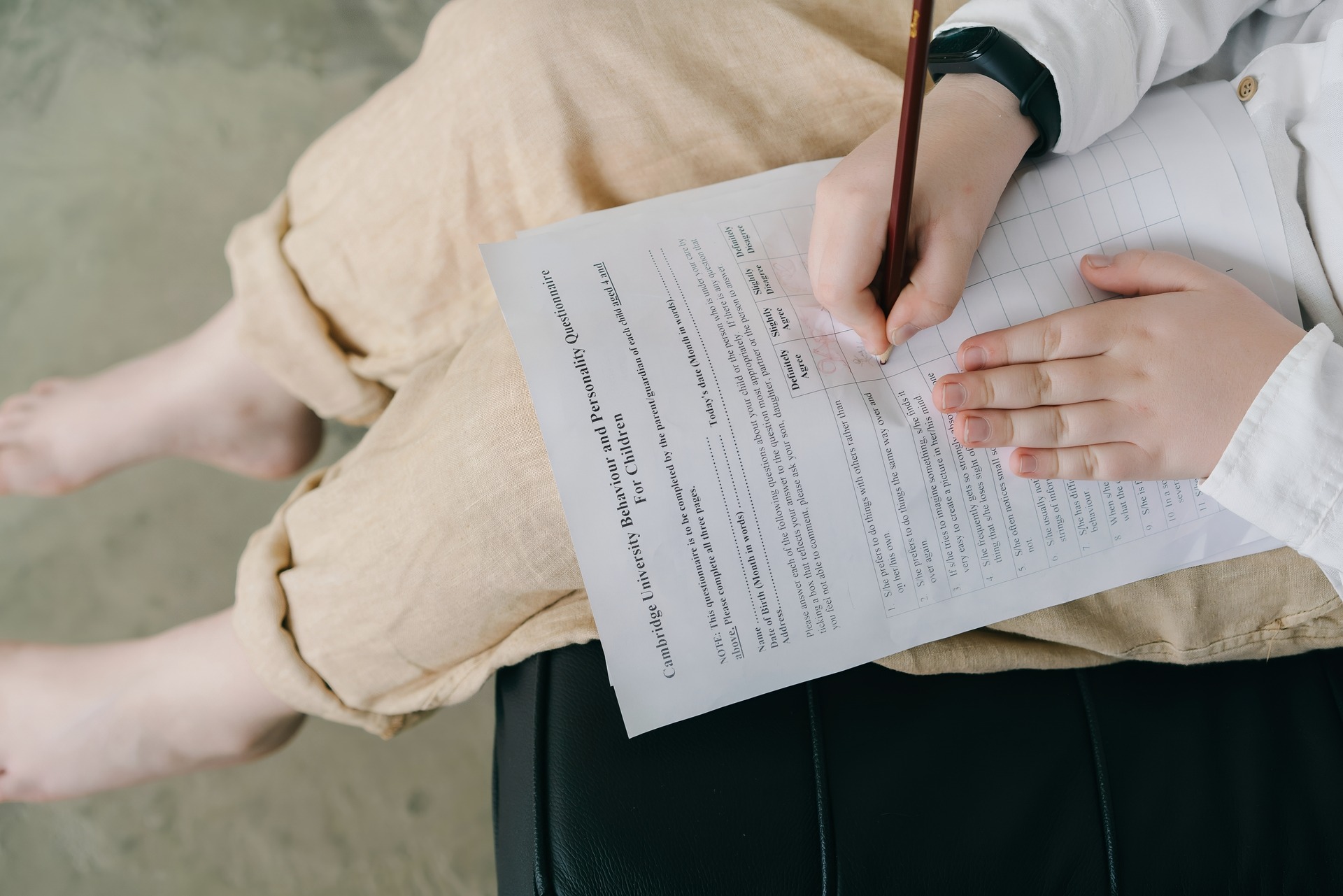
有一类量表是医生通过观察来进行评定的,比如,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但即使是患者自评量表,除了患者的主观因素之外,医生仍面临着一些主观性的判断和选择。
何况,量表作为诊断后的验证是比较合适的,从来都不可以用于直接诊断。
诊断标准的变化对医生的影响也很复杂。诊断标准的放宽,特别是鉴别诊断的标准放宽,对医生来说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宽松的标准降低了医生做出误诊的概率(确切地说,只是降低了医生负误诊责任的概率)。如果做出肯定诊断时负误诊的概率降低,而做出否定诊断时负误诊概率的升高,那么医生是否更倾向于做出肯定的诊断?


药物
还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医生的判断。例如药物。
药物是治病的工具,就好比武器是杀人的工具。
社会心理学家伯克威茨 1978 年的一个研究发现,当侵犯者手边有武器时,侵犯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身边没有武器的情境。这就是著名的“武器效应”。
简单讲,“武器效应”说明了一个道理:两口子吵架地点万万不可选厨房。
然而,“武器效应”仅仅能够解释侵犯行为吗?可以想见,一个医生有药可用和无药可用时,心态很可能会不一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现在精神科医生对人格障碍的诊断都非常谨慎,尤其是传说中的“双重人格”“多重人格”,尽管某类影视作品和网络小说中,这类角色比比皆是,但现实中几乎很少看到。
或许在潜意识里,一个医生会避免做出让自己“无能为力”的诊断。
反之,如果一种病有药可用,情况可能会反过来,医生也许会更倾向于做出诊断。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医生都是自私的,这只是一种推测,一般是发生在说不清的潜意识里的东西,而且很可能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有关。
最后,药企资本的运作也可能与抑郁症的诊断“泛化”有关,但这也只是逻辑上的推测。
医生的工作环境也限制了医生对抑郁症诊断的全面性和精准性。试想如果医生可以像咨询师一样,每个病人聊上一个小时,一天接待不到 10 位病人,这对医生本人未见得是很大负担,但对排队候诊的病人却是难以接受的。
资源永远稀缺,医疗资源在我国尤其稀缺,为保证公平,医生这个位置,不会允许他为每一位患者做出精细的、个性化诊疗方案,面向如此巨大的需求,医学模式只提供共性的、统一的、程式化的解决方案也完全可以理解。
当然,这种妥协使得医生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标准的复述者,并不利于对抑郁症的深入研究。
医生对面的人
医生对面的人,尽管我们一般就称为病人、就诊者,但它们绝非等价的概念。因为你的很多有意无意的选择,也会影响医生是否在诊断证明书上签字。
比如你如何看待成为抑郁症患者这件事?这涉及所谓“病耻感”;又如,抑郁症对你来说有没有显在或是潜在的某种好处?这涉及所谓“继发获益”。


就诊者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而来,携带着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心态、这些故事在医学诊断中几乎不可能被重视。
回答医生提问和接受量表测评时,人的各种心理也都可能对诊断结果产生影响。
“病耻感”无疑会让某些人对自己的抑郁症难于启齿,这让他难以被身边的人识别为抑郁症患者,甚至也可能使他放弃或拖延去医院就诊,这使得抑郁症患者的统计数字与真实数字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对某些人,抑郁症这个标签也不见得全无益处。某些时候,这会使得他自身的“不对劲”获得一个解释,可能比全无解释要好。 还可以想见,抑郁症可能成为一种有意获利的理由,尤其是在诊断标准限于症状,且不断放宽的情况之下。
他者
他者无他,主要是身边的人、机构媒体,以及他们在传播的信息。对抑郁症的污名化、误解、抑郁症所指的泛化都将影响人们对于抑郁症患者多少的感知。
前面提到的“病耻感”“标签化”其实都涉及某种价值判断,而我们的价值观无疑与他者话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我们遭遇到一个悖论:我们只能作为自己而活,但又根本不可能作为自己而活。我们无法作为别人而活,因为我们只有自己这一个生活的主体,但我们其实又到底不可能只作为自己而活,因为不存在一种价值观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可以让自己坚信它是我们独有的。
传统的观念总是将精神病人视为异类,在他们的逻辑链条中,抑郁症=精神病=疯子和变态。深受“心物二元”“眼见为实”影响的人,或许仍旧觉得抑郁症只是“矫情”,只是“装”,当然在他们看来精神世界里的一切都具有某种虚假性。有一些人会因此害怕抑郁症、忌讳抑郁症,畏惧与忌讳,其实都是对这种观念的认同。


一些仅仅是体验抑郁情绪的人,因为“抑郁焦虑”,会觉得自己患上了抑郁症——这使得“得了抑郁症” “我抑郁了”之类的说法日益泛化。
90 年代以前,若是听到某某人自杀了,人们的直觉往往是投资失败、东窗事发、失恋等等,今天,几乎总会首先想到抑郁症。
人们对抑郁症的理解未能去伪存真,反而变得暧昧不清。甚至一些专业性的表述,都会引人误解,比如“每多少多少人就有一个抑郁症患者”,这是在完美统计分布的情况下的理想状态,当然不见得在一两次抽样中就得到验证。这个说法本身也无大错,但对于普遍不太了解统计学的大众来说,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这大概是传播抑郁症知识的媒体和机构需要反思的事情,人们对于一件事物的看法,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它的感受,进而引发自我证实、选择性无视等效果,抑郁症的去神秘化仍然在路上。
写在上面的,其实只是对于抑郁症患者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真实数量的某些猜想,其中有很多因素造成这个特殊的心理问题难以准确计量,或者,对于公众来说,难以形成靠谱的估计。但是,无论怎么讲,抑郁症已成为没有人可以忽视的存在,哪怕他从来没亲眼见过一个抑郁症患者。面对这一指向全人类心理健康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Use,WHO(2017). 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WHO/MSD/MER/2017.2
[2] Huang, Y., Wang, Y., Wang, H., Liu, Z., Yu, X., Yan, J., Yu, Y., Kou, C., Xu, X., Lu, J., Wang, Z., He, S., Xu, Y., He, Y., Li, T., Guo, W., Tian, H., Xu, G., Xu, X., Ma, Y., … Wu, Y. (2019).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The lancet. Psychiatry, 6 (3), 211–224. https://doi.org/10.1016/S2215-0366(18) 30511-X